
许多人了解王昱珩,是在综艺节目上。在那些节目里,王昱珩的身份通常是「天才」或是「鬼才」——他的记忆力和观察力超群,毕业于清华美院,但一天班也没上,宁愿当个闲人。与此同时,他幼时患谱系自闭症和右眼视力骤降到0.4的经历,让这些身份又多了一层神秘。但仅仅如此的话,你依旧很难解释,为什么综艺节目中各类天才不断出现,王昱珩依旧是王昱珩,多年过去,无人能够取代他。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让人们记住他。
这份独特,也让许多人难以理解他,因为他的活法与众不同。他认为每个人的绽放都有自己的方式,他自己也一直在走一条特别的、只属于王昱珩的路。比如,毕业后他没有上过一天班,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与自然的相处上。在如今这个时代,讨论「三十岁提前退休」,亦或是回答「人生是轨道还是旷野」,都是热门话题,而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想明白了这些问题。
今日立夏,特仑苏携手博物画大师曾孝濂,共创「24节气联名」系列产品,邀请设计师王昱珩与我们分享他的自然之道。他在与自然的相处中获得滋养,也获得了坚持自己活法的力量。
夏天,以及绽放
立夏一到,王昱珩的难题就开始了。
对于拥有一个堪比小型植物园的院子的他来说,如何「过夏」是压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。尤其是这个几十平方米的院子里,已经栽入了成千上万株植物。北京的夏天光照过于充足,又极其干燥,这种环境会将院子里大量的植物晒伤、晒死。这使得他总在想办法让这些植物活下去。「我一直在自己家里与天斗、与地斗,做这种逆天的事情。」而现在,王昱珩要对抗的是夏天。
在养植物这件事上,王昱珩不仅专注,而且极致。夏天的阳光之所以对他的植物杀伤力大,很大一个原因是他种的植物品种太多了,光在院墙上,他就立体摆放了2400盆花。单看这数量,就已经超越了普通爱好者,更像是在建立一个多样性的植物品类库。比如,玉簪是北京小区绿化中常见的一种花,一般只种一两种,但王昱珩不,他在家里种了几十种玉簪,一到夏天开花季,白的、紫的、粉的……五颜六色都有,玉簪叶子也是各种各样,除了最常见的绿,还有白的、金的、黄的,甚至还有蓝的。这种极致,还不止体现在花上,就连种树,也是要多种多样。比如他在院子里种了近五十种枫树,甚至院子因此都叫「枫人院」,他特喜欢这名儿。但种这些枫树相当困难,一般来说,只有同时具备耐晒、耐旱、耐寒特点的品种,才适合在北京种植,而一些对温湿度敏感的枫树则很难活,所以他的枫树经常死去。不过他不甘心,「我会千方百计去尝试,枯木有时候也可以逢春的」。
而要对抗夏天,数量巨大和品种多样带来的分层化管理只是难度之一,更难的是要用「顺其自然」的方式避暑。一般人可能会想到用人工遮阳棚防晒,但王昱珩偏不,「我总是希望不要有太多人工的痕迹」。他希望「让花成花,让树成树」,让所有植物以最自然的方式生长。所以,他如今正在忙着修剪院子西侧生长的紫藤,让它们的叶子给枫树们提供阴凉,而这种「顺其自然」也回馈了他,「阳光透过叶子,光影通过水面反射到墙上,波光粼粼的,很美」。
所以,在王昱珩的这种「顺其自然」的过夏方式中,种一些适应暴晒的植物就很有必要。而在所有耐晒的植物里,杂草是相当特别的一种,因为不会有人特意在院子里种杂草。但王昱珩相当喜欢杂草,也想种一大片。「在阳光最好的地方,别的所有的植物在这个地方都活不下去,都会被太阳灼伤,但比如狗尾草就没有问题。狗尾草也叫光明草,它可以在烈日下摇曳,即便被太阳晒弯腰,也不会匍匐和卧倒。」

他甚至想找一个院子,专门种各种杂草。他的愿望之一,就是三年以后在上海弄一个种满杂草的院子,与北京的「枫人院」呼应。连名字都想好了,就叫「蘅芜苑」,与红楼梦里宝钗的院子同名。「上海是一个常绿的、精致的城市,但我反而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不同的院子,这个院子里面全是杂草,狗尾巴草、狼尾草、芦苇、香根草、蓝羊茅……院子里都是草,就一定荒芜吗?其实未必荒芜,反倒我觉得很梦境。」
他说自己总在追求「一种冲突感」,因此似乎总是拧巴着。某种意义上,就像他帮助植物对抗夏天那天,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现实。
窗户外的绿色
王昱珩小时候许多回忆都与夏天有关。
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,王昱珩一家住在集体分的房子里。「那时候暑假在北京是很难熬的,好不容易盼到了放假,感觉时间应该属于自己,但后来发现全是作业,而且天气也热,没有空调,没有电扇。一家三代人挤在一张床上,睡觉时轮流扇扇子。」
这种生活让王昱珩养成了节俭的习惯。「我吃饭只要掉一粒米饭,下一刻,我父亲就会很严厉地纠正我。」这也使得他长大后,虽然购买植物花费不少,却选择用「以玩养玩」的方式。他会自己繁育植物,甚至动手嫁接,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换。而这也要求他更懂植物,要比其他人养得更极致。
那时候没有阳台,唯一能种植物的地方是窗台,于是父亲焊了个架子,又把窗台扩张出去了一部分,家里要吃什么,就种什么。这给小时候的他心中种下了一粒亲近自然的种子。那么小的一个窗台,竟能种上小葱、辣椒、黄瓜、丝瓜、葫芦、西红柿等等近十种蔬菜,「所以我们家一直有菜吃」。更绝的是,连葫芦都种,结果葫芦老是爬到别人家窗户那边去,「我妈就会随时把那个葫芦秧扯过来,该去头去头」。这些画面如今仍历历在目,由于窗户边就是全家唯一一张桌子,一家人吃饭、他做作业也都是在窗户边,「所以,我感觉我看向外面的时候,就一定会透过这么一个绿色画框」。
而透过这个「绿色画框」,还能看见楼下的一棵大槐树。那是院子里最大的一棵槐树,树干粗大,要好几个孩子才能抱得住。他小时候捉迷藏、捉蛐蛐、躲雨……都是在这棵大槐树下,可以说,这棵大树陪伴了他的成长,亦是他的伙伴。「所以我觉得在人住的地方,院子里一定会有棵大树,但很可惜,前段时间我再去院子里,那棵大树已经死了,树干还在,但是一片叶子都没了。我就觉得很伤感,你知道吗?我看了它四十多年,然后在这之前它肯定也活了许多年,但是它现在也没了。」
他是个相当念旧的人。「甚至长大以后,我收藏的所有东西都和童年记忆有关。」虽然他没法在院子里种下那棵大槐树,但他种下的紫藤跟这个有关,「其中有一棵紫藤就是纯白的,它开花时,满院子都仿佛是槐花的香味儿啊,它们的香味很相似。我就觉得它会治愈你,因为它会让你产生一种对于时空的连接。」
这种回忆与现实的时光交错感,他能够非常敏锐地感知到。「时间是庸医,却可以包治百病,时间不是解药,但是解药就在时间里。时间扑面而来,我们终将释怀。所以,我在养植物的时候,就是在体味时间,就是我能够让时间在这一刻具象化。」
也是在那段时间,王昱珩慢慢发现了属于他的生活方式和快乐——相比于人的不稳定,植物的稳定性让他觉得安心,「植物我给他施氮肥、钾肥、磷肥,那我就知道它的叶子要茁壮了,它的茎要变得粗壮了,花要开了,基本上你付出什么,就可以得到什么。」

而与人相处,却常常会带给他孤独。「你跟一个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,大家都特别好,然后接触接触就会发现,慢慢有问题了,然后可能就慢慢走散了,不联系了。最后的结果就是沉默与孤独。」但植物不同,四季变化,「它们总会再来一次,就像日落之后必然有日出,春夏秋冬之后必然还有春夏秋冬。」
某种意义上,植物成为了他与现实之间的锚点,甚至是一种羁绊,而这只是个开始。
烟花和炭火
明白了王昱珩与植物之间的这种连接和羁绊,就能够理解他身上那种特有的疏离感。
《人物》与王昱珩见面是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处小型植物园。这次访谈,缘起于特仑苏携手博物画大师曾孝濂,共创「24节气联名」系列产品,其中关于夏天的花朵里,就有王昱珩很喜欢的光明草,也有他小时候很喜欢吃的西瓜。
我们发现在与王昱珩的交谈和拍摄过程中,每当到了某个暂停的阶段,别的嘉宾一般会抓紧时间休息,但他却是抓紧时间看各种植物,遇到喜欢的还会与店主交流养花心得。比如,在植物园大厅里正中央的房梁上,挂了一盆鹿角蕨,这是王昱珩非常喜欢的一种植物,「因为不管你是什么人,你要观赏它,都必须仰视它」。他抬头看了这盆悬挂在高处的鹿角蕨好半天,甚至还询问了它是否出售,以及多少价格。你会看到,他谈论植物时的精神状态和语言密度,明显高于谈论其他事,那种笑容是写在脸上的开心。
其他大部分时候,王昱珩是平静的。他说话的语速不快,声音也不大,但他的表达非常真实。我们这次做的是一次与夏天有关的访谈,他无论是聊到被众人关注认可的时刻,还是之前因不被理解而沉默的时刻,都是同样的温和,既没有喜悦,也没有沮丧。就像他说到自己曾经面对人生中的夏天时,「阳光太强烈的时候,我知道应该去遮阳,需要去避开。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蓄力,什么时候不要冒进。(烈日)之所以灼心,是因为(人)不够安静。人之所以感觉到燥热,是因为把自己暴露在了阳光之下。」
如果把每个人的成长比作植物,最重要的是,每个人都必须想明白自己是哪一种植物,以及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绽放方式。正如那句话所说,「夏自有光,我自绽放」。毕业后,相比较于挣钱谋生,王昱珩花了更多时间与大自然中的其他生命相处。在这种节奏下,他没有被烈日和暴雨影响,活成了自己希望活成的样子。
不过,人生中总有意料之外的变化和挑战。他的这种原本低调的生活方式,在2015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「我的夏天非常短,在我的人生中几乎一闪即逝。我在2015年上节目,突然之间有一天被大家知道了,我认为那可能是我人生中的某一个绽放点。当时我一个月推掉了很多的活,在这一刻我需要的更多是克制。」

他用烟花与炭火的比喻,来描述绽放的方式。「烟火固然美丽,但一转即逝,而炭火它就比较长久,所以我觉得绽放一定是一个多角度可以去理解的东西,它可以是一个结果,让你一下子看到,它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过程。琉璃易碎、彩云易逝,越是(烟花)这样的东西,越是来得快、去得也快。」
这个节目已经播出整整十年,如今回看,能被记住的人并不多。比起一闪而过的烟花,王昱珩的确更像炭火,一直在持续燃烧着。与许多人短时间里大量追求名利的做法不同,他面对这些有很强的克制力,「永远都不要让自己轻易地就到了一个顶峰,月满则亏,水满则溢,在这种盈亏之间,我觉得自己要知道自己是谁,还有什么时候适可而止。就像我们做设计一样,如果把所有人认为美的、好的都堆砌在里面,一定不是好的设计,反而是最差的设计。」
所以,在王昱珩眼中,无论是姹紫嫣红,还是断井颓垣,都有自己美的地方,区别只在于观看的人和角度。「我蹲在地上看到台阶石缝处钻出来的青苔的时候,那一刻给我的惊喜和视觉冲击,不比姹紫嫣红弱。因为它在那一刻,像一股暖流一样,是能够直击你的心田的,而有些时候,姹紫嫣红虽然把眼睛填满了,但如果那一刻不能流进你的心房,其实也没什么意义,你也可以视而不见。」
他依靠这种信念,在这个许多人都困于「焦虑」「内卷」的时代中,在这种如同夏日烈日灼心一样的阳光中,获得了一种充满疏离感的平静。哪怕后来知名度变高,他似乎也仍然我行我素。「很多时候你干的那些事儿,在不理解你的人眼中,都没什么用,但是也总会有人很欣赏你。所以你就做好你自己就行了。」他从这些年的经历中领悟到一个道理,就是不去期望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。「如果你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的话,总会有人看见你,就算没看见,也没关系,因为你知道你是谁,这就够了。」
这也是这些年与植物相处带给他的启示。植物生长的确需要阳光,但过于猛烈的阳光,过于丰富的肥料,最后一定不是好事。他更宁愿像炭火一样活着。所以,夏天也可以是长久的,就像现在所有人看到的「水哥」王昱珩,也是靠多年的时间沉淀。「我被大家所认识,这一切一定不是爆发式,所有包裹其中的能力、资源、时间,都是沉淀在我人生土地里的养分。」
生态共存
而无论是绽放,还是与夏天或植物的相处,王昱珩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——在任何情况下,都选择做本来的自己,他相信,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绽放方式。
此次特仑苏推出了「24节气限定」夏系列主题包装,并选择了生长在夏日的六种植物作为主角,通过曾孝濂先生入魂的笔触,六种植物各自绽放出最美的生命力,让王昱珩深感共鸣:
立夏之初,田间的光明草舒展翠叶,正如《淮南子》中所写「蝼蝈鸣,光明草生」;小满时节,韩愈笔下「照眼明」的石榴花,化作红玛瑙缀满枝头;芒种麦黄,熟小麦低垂,像是大地的金簪;夏至阴阳交割,半夏花开,一茎三叶,悄然挺起白穗;小暑荷风,观莲消暑的人们回味着「出淤泥而不染」的名句;大暑炎威,冰镇西瓜被沿着翡翠纹剖开,奉献一汪清甜。
特仑苏的这次联名,希望从自然中萃取「养分」,为人们带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滋养:以更极致的物质营养滋养消费者的身体,也以触动精神的方式滋养人们过夏天的精气神。无论是联名的六种植物的绽放姿态,还是以植物为师的王昱珩的「绽放」之道,都让我们看到,能以自己的方式绽放,就是最耀眼的活法。而好的牛奶也是如此。
「夏自有光,我自绽放」,「这一理念」也反复在自然界得到验证。近几年,王昱珩花了许多时间在与自然有关的节目上。在第一季的《大国之树》纪录片中,他着重对比了两种森林,一种是自然生长的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,另一种是人工干预种植的橡胶林。
在热带雨林里,身体上附生着兰花的望天树让他欣喜,生命以自己的方式美美与共。望天树长得最高、最快,是一种标志性的植物。「它像一张撑起的大伞,把底下所有的空间都给了其他植物,带来完整的生物多样性的群落。它既能够接受到第一滴雨水,也可以帮助到其他生命。」相比之下,西双版纳的橡胶林则令他心痛,那里没有风声、没有鸟叫、没有虫鸣,只有滴答滴答的橡胶声,「这种人工种植的单一树林,生态系统就很脆弱」。
这也与他坚持帮植物们用自然的方式度过夏天很像,他排斥人工干预,想让植物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,而这一面对他来说才是最美的。
以植物为镜像,王昱珩这四十多年只是在做一件事——让王昱珩成为王昱珩。特仑苏亦是如此,这么多年始终坚持把更好、更自然、更高品质的牛奶带给消费者。用水滴石穿的方式,坚持做对的事情,用数年如一日的姿态,慢慢打磨和沉淀品牌。这种「润物细无声」般的慢,反而是一种快。
正如王昱珩所说:「寂寂生,好好活,慢慢来。让花成花,让树成树,你也会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,自然会更好绽放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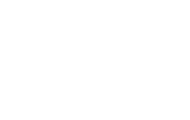
 观念流
观念流 微信关注,获取更多
微信关注,获取更多